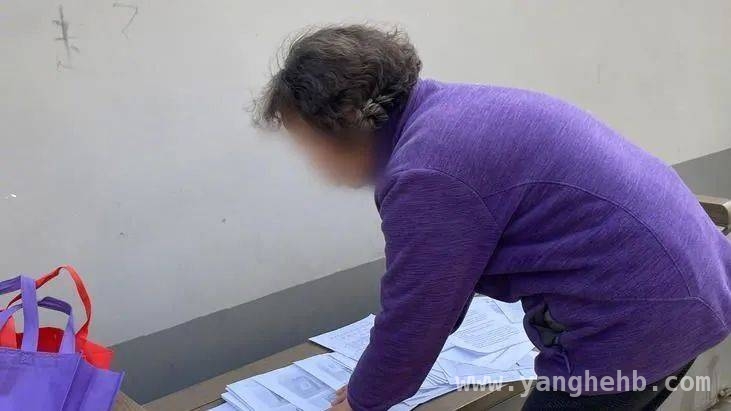本文围绕祝勇所著的《国宝》展开,讲述了该书创作的起源、过程,以及其在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方面的独特之处。从《故宫文物南迁》到《国宝》的转变,展现了作者在宏大历史叙事中挖掘个体故事的努力,也体现了作品在文体重构、细节呈现等方面的亮点。
有这样一位作家秦雪莹,她关注着一部特别的作品。今天,我们要聊的便是祝勇所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宝》。
在2022年初春,祝勇完成了30万字的非虚构文学《故宫文物南迁》并将定稿交给编辑部。这一行为,仿佛是他递出了一卷沉甸甸的时空长轴。为了能够精准捕捉这段历史的呼吸,祝勇可谓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踏遍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辗转于辽宁、重庆、上海、四川等多个地方。他不仅叩访了文博前辈的后人,还率领纪录片团队重走了南京、宝鸡、贵阳等地的南迁故道。在他翔实的考证之下,运输路线就如同精密的罗网一般清晰,文物清单好似无声的军阵排列整齐。就这样,1933年至1958年故宫文物南迁的轨迹得以完整复现。
祝勇始终认为,即便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依然存在着文学书写的广阔空间。那些个体的悲欢离合、家族的聚散飘零,就如同暗河一般在时光中静静流淌。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思考,催生出了他创作《国宝》的强烈冲动。当历史学者用经纬度去标记文物迁徙的坐标时,祝勇这位小说家却听见了铜器在蜀道夜雨中发出的嗡鸣,看见了守护者捧着《快雪时晴帖》真迹时那颤抖的指尖。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撕扯与碰撞,最终促使他完成了从《故宫文物南迁》到《国宝》的大胆纵身一跃。
《国宝》的创作过程无疑是一场艰辛的文学苦旅。小说初稿由于过于贴近史实,在情节和人物塑造方面稍显不足,因此收到了不少修改意见。这对于任何一位作者来说,都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然而,祝勇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果断地对初稿进行修改,大到情节架构的调整、人物关系的重塑,小到一个词语的选用、一个标点的斟酌,他都一丝不苟。谢锦老师“太纪实了,不够飞扬”的冷水,梁晓声先生“虚实分寸”的提醒,再加上祝勇毅然从30多万字删至16万字又重新出发的决绝态度,共同锻造出了这部作品叙事的精度。
这场文体重构的本质,实际上是学者与小说家之间的一场自我博弈。当世人都在凝望紫禁城朱红的宫墙时,祝勇的笔锋却悄然刺破了时光的褶皱,直接抵达了1933年那个雪落无声的北平寒夜。在那个寒冷的夜晚,1.9万箱文物正悄然南迁,车轮碾过积雪的声响,既是文明在战火中低沉的呜咽,也是民族根脉在绝境中迸发的裂帛之声。
202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恰逢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双重纪念时刻。而《国宝》的诞生,就犹如时空隧道的共鸣箱。除夕夜北平的炊烟、南迁途中的枪炮声、西南深山的孤灯……这些曾经冰冷的历史细节,在祝勇的笔下不再是历史档案里毫无生气的注脚,而是浸透了体温的鲜活记忆。难能可贵的是,祝勇以故宫人特有的敬畏之心消解了小说的传奇性。比如石鼓搬运的危机不是靠壮举来化解,而是依靠几代匠人积累的文物打包技术;主角的觉醒时刻也并非在恢弘的历史现场,而是在古物鉴定与守护的历程中逐渐坚定。这种植根于文学与艺术专业背景的写作自觉,让《国宝》在当下的历史小说中显出了珍贵的异质性。
此刻,窗外北京城的灯火如同星河般流淌,映照出案头这60万字所凝铸的万里山河的璀璨。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力量,就在于它让我们看到:当历史的惊涛拍打文明的堤岸时,总有人愿意以血肉之躯筑起精神的方舟。在山河破碎之处,文明以人的形态得以重生。这或许就是文学的伟大之处——从泛黄的故纸堆里,雕镂出一个民族的文明尊严和永不熄灭的人性之光。
本文围绕祝勇的《国宝》展开,介绍了创作背景、过程及意义。从《故宫文物南迁》到《国宝》,体现作者在宏大叙事中挖掘个体故事的尝试。创作虽历经修改,但文体重构使其更具深度。在特殊纪念时刻,《国宝》让历史细节鲜活,以独特写作消解传奇性,展现文学让文明以人形态重生的伟大力量。
原创文章,作者:Megan,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anghehb.com/19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