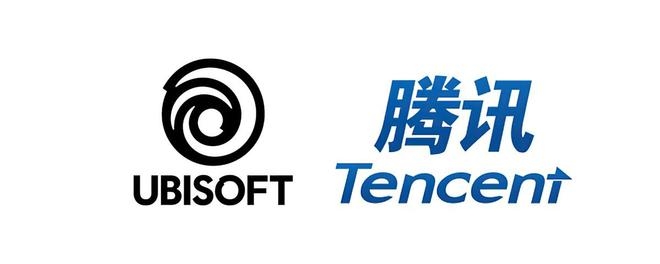本文通过作者买到的《北京市商品目录》及相关资料,讲述了其中记载的各种商品名目,进而引出对过去老北京百姓日常生活用品的回忆,如暖水瓶、铝壶、搪瓷制品等,展现了过去生活的特点和变迁,最后提及“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

作者止庵几年前在旧书网上购得一本特殊的书。说它是书,却没有版权页,也没有定价,但整体完整无缺,品相还很不错。其封面印着“北京市商品目录 北京市编制商品目录办公室编印 1960.1”,是十六开精装的一册。
印了朵花的铁壳暖壶
书的卷首“说明”中提到:“为了更好更全面地安排人民生活消费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并为进一步研究商品分类、行业分工、商品分级管理等,在中央商业部商品目录编制办公室的领导下试编了北京市的商品目录。本目录共分为 90 大类 673 个品目 29926 个品种 166026 个细目,基本上反映了北京市日用工业品及农副产品的生产面貌和人民生活消费方面丰富多彩的需要。”
在旧书网上还有一本标明“内部资料”的《商品目录(草稿)》,署“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商品目录编辑组编印,1960 年 1 月”,是简装上下册。从商家提供的图片来看,其分类和内容与《北京市商品目录》稍有差异。
这两种资料似乎并不属于“年鉴”,因为至今都未查到别的年份出过类似的东西。作者也不太明白为何偏偏在那时编制这样的资料。不过,作者觉得其中记载的各种名目很有意思。“说明”还提到:“本目录编制的商品以人民消费品为主,凡吃、穿、用、烧、观赏的商品,力求完整齐全。”友人藏书家谢其章说,这本书像辞典似的又厚又大,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可能毫无用处,但他却读得津津有味,还回忆起从前许多生活细节。作者对此也深有同感,这本书便成了他们的谈资。虽然所聊的或许算不上“旧书新知”,只是“旧书旧知”,但这些旧知如今人们已不太知晓,重新提起也就成了新知。
作者姑且从“暖水瓶及日用玻璃器皿类”的暖水瓶说起。从前作者读过罗兰·巴特 1972 年四五月间所写的《中国行日记》,其中不止一次提到暖水瓶。尽管距离《北京商品目录》编纂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消费品方面实际上变化并不多,作者下面讲的也是巴特那个时候或稍晚一点的事儿。巴特 4 月 12 日刚到北京就写道:“偶像物件:沏茶用的大热水壶,外皮上印着花,姑娘和小伙子手上都有一把。”14 日在北京参观一家商店时,“我们受到了欢迎。……带有柳条编织外罩的大热水壶。”译者注:“这里所说的‘柳条’,很可能是作者对于‘竹皮’的误判。”19 日在南京参观公园内一处儿童绘画与书法展览,“一幅图画:在一个热水壶(还有两只玻璃杯子)上画着南京大桥。最终,还是热水壶……”26 日在西安,参观一个模范家庭,“当然,还有外皮有花卉的暖瓶!”28 日在北京参观另一家商店,又提到“竹编热水壶”——由此可知巴特也认出瓶壳是竹篾而非柳条编的了。当时无论单位还是人家,暖水瓶除了实用之外,还是一件必不可少的摆设,巴特称其为“偶像物件”,真是很有眼力。
这里提到的金属壳和竹壳两种暖水瓶,在《北京市商品目录》中均有记载,北京人称之为“暖壶”。家用的暖壶大多是五磅的,至少得有两个。水烧开后会贮存在暖壶里,用于沏茶、洗脸、泡脚和冬天洗衣服等。每晚睡觉前,尤其是煤炉封火前,一定会烧水把暖壶灌满。每次灌暖壶前,都会把壶底混有水碱的剩水倒掉。作者还记得开水灌入壶中的声音以及将满时声音的变化。不过,作者的父亲不喜欢用隔夜的暖壶水沏茶,每天早起都会现烧开水,称之为“鲜开水”。铁壳暖壶除了铁皮表面涂绘如巴特所见的那种,还有一种是用镂空薄铁片焊接而成的,外形特别粗糙。金属壳和竹壳暖壶都装有固定把手,有的还有活动提手。暖壶口有瓶塞,“说明”中称是“钢精包布”,用久了就只剩下一截软木圆柱。有时半夜瓶塞会突然弹起,砰的一声,扰人清梦。暖壶内的瓶胆非常脆弱,作者小时候就不止一次不慎踢倒暖壶,碎玻璃和热水洒了一地。即使只是磕坏瓶胆底部突出的玻璃尖儿,暖壶就不保暖了,只能更换瓶胆,商店里也有卖的。铁壳暖壶容易锈蚀,竹壳暖壶不结实,大约到 1980 年代后期,才有红、绿、蓝等颜色的塑料壳暖壶出售。但作者看北井一夫摄影集《1990 年代北京》中注明“1997 西城区南篦子胡同”的一幅照片,所摄人家玻璃窗内摆的还是印了朵花的铁壳暖壶。
将爆米花倒进浅儿里
过去烧水大多用铝壶,也就是《商品目录》“日用搪瓷及铝制品类”中的大肚生铝壶;此外还有铝锅、铝炒勺、铝制饭盒、铝背壶、生铝盆等,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物品。前文提到的“钢精”其实就是铝,董树人《新编北京方言词典》中有“钢种锅”,“钢种”惯常读“gāngrǒng”。作者有些关于这方面的记忆写进了长篇小说《受命》。一是北京水质很差,用铝壶或铁壶烧水,没多久壶内就会形成厚厚的水碱,甚至会把壶嘴堵住。“回到屋里,冰锋在炉子上烧了一壶水,换了块除水碱用的消毒棉花泡在里面。”这是作者所在院子里邻居的方法,如果觉得这样的水不好喝,就只好隔段时间硬把水碱敲掉。二是铝壶、铝锅用久了会有所损坏——多半是底部烧漏,这时会有走街串巷的手艺人来修理。“他们出了院门,不远处有个老师傅正在吆喝:焊洋铁壶嘞!有钢种锅换底!身边放着一副挑子,一头是个生着火的铁炉子,上面坐着壶水;另一头是装着铁砧子、黑白铁板和铝板的木箱。”三是作者在 1980 年代初在医院口腔科上班,每天都要劳母亲早早起来做饭。“休息室里有个很大的高温柜,用于消毒托盘、探针、镊子、口镜之类,辟出一角,供医生护士们加热带来的饭菜。大家工作向来很忙,中午常常连去医院食堂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冰锋打开高温柜的门,里面有一大一小两个铝饭盒,分别装着米饭和炒菜,菜是青椒鸡丁和西红柿炒鸡蛋。一看就知道是早上现做的。”
日用搪瓷制品也很常见,比如《商品目录》中提到的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盖杯、搪瓷大盆、搪瓷小盆等。作者考上大学在胡同里也算是件大事,有街坊赠送了两个脸盆,一个是红边白底,中心绘有牡丹,还有个“红双喜”;另一个是白色的,分别用于洗脸和洗脚,作者用网兜装着带去了宿舍——《商品目录》“日用线货”项下写作“网斗”,它是用麻绳或线绳编成的,后来又有了尼龙绳的,也是当初常用的物品。在家里,脸盆放在“铁制日用杂品类”的铁脸盆架上。搪瓷盆漏了,胡同里也有手艺人修补,如果只是磕掉块瓷,自己涂点漆就行了。这一类里还有两样东西值得一提,一是痰盂,一般用于公共场所,比如医院、学校、剧院以及单位办公室。作者去人家拜访时也见过,后来写进了《受命》:“南边第一个门是书房,门开着。一个很大的写字台,旁边是一长排书柜,一对褐色的真皮沙发,中间摆张茶几,前面放了个痰盂。”痰盂内盛着小半盂水,除了吐痰,还可以扔烟头。二是尿盆,与痰盂形状相近但稍矮,《商品目录》写作“便器”,因为公共厕所在胡同里,尤其是冬天起夜不方便,所以尿盆是住平房人家必备的物品。王小波《我的阴阳两界》写道:“在胡同口碰见一位少妇,正在倒尿盆。”其实每天天亮时,胡同里有很多人端着尿盆直奔公厕,无论男女老少。
那时讲究的老房子会铺木地板,还有拼花的,一般的则铺方砖,差一点的只抹水泥,甚至直接裸露土地。不管是哪种地面,主客人进屋很少脱鞋——直到后来大家纷纷搬进楼房才养成了脱鞋的习惯。《商品目录》“棕藤荆柳草及其制品类”中有高粱苗笤帚,“铁制日用杂品类”中有白铁簸箕、黑铁簸箕,都是用来扫地的。白铁的不会生锈,但比黑铁的贵,作者小时候家里没钱,舍不得买。笤帚用到近乎秃了——被称为笤帚疙瘩——才会换新的。还有高粱苗炕笤帚是用来扫床的。“木制和铁制家具”中有弹簧床、木板床、行军床等,作者都睡过。作者家还曾有过一张棕床,只有四条木腿的床帮上架着个棕床屉,也不知是不是从信托商店买来的。家里的洗衣盆是很早买的白铁的,用了很多年都没坏。与之配套的是“木制日用杂品”的洗衣板,北京人称之为“搓板儿”。最难洗的是双人床单、被里之类,需要一截一截地挪动,打肥皂、搓洗,才能在洗衣盆里洗干净。搓板用久了沟槽会磨浅变平,胡同里也有手艺人用一种专门的家伙事儿重新铳出凸槽来修理。“棕藤荆柳草及其制品类”的“柳编器”中有菜浅、浅子,作者曾在《受命》中写过:“这时已近黄昏,做木工活的收工了,原地换了个崩爆米花的。一尊黑乎乎的大炮似的爆米花机架在支架上,下燃炉火,师傅一手拉风箱,一手转动爆米花机。有个梳着两个髽鬏的小女孩一脸渴望地站在跟前。嘭的一响,腾起一团白烟,师傅举起肮脏得已成黑色的口袋,将白花花的爆米花倒进她端着的浅儿里,一股香喷喷的味道。”书出版后不止一位读者问“浅儿”是不是错字。这是一种柳条编的平底浅帮的器皿,比通常见到的笸箩更浅。高艾军、傅民编《北京话辞典》收录了“浅儿”“浅子”,并注明后者“又作‘浅儿’”。走街串巷的手艺人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弹棉花的、锯盆锯碗的、磨剪子戗菜刀的,他们不时吆喝几声,音调各异,从当街传入各户人家。
百姓日用即道
“铁制日用杂品类”中的熨斗,作者曾陪外婆去附近街上的裁缝铺做衣服时见过师傅操作:师傅把铸铁实心熨斗放在炉子明火上,烧热后拿起,朝底部吐点唾沫,以此判断温度是否合适;然后含一大口水,噗的一下喷洒在做好的衣服上;再戴厚布手套的手攥住把手,匀速推移熨斗,大小褶皱就会依次熨平,轻重都在师傅的掌握之中。熨斗放凉了,就重新在火上加热。作者对这段记忆特别清晰,因为师傅每次喷水都带有浓重的口臭。
“文具类”也有一些值得一说的东西。横格信纸、直行信纸、航空信纸,横式信封、直式信封、航空信封,这些都是经常会用到的。还有稿纸,红或绿格的,四百字一页,要属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的最好用,作者父亲在外地时,还让他们买了寄去。别的稿纸纸质有时不太好,作者父亲有篇文章写道:“我怕用一碰墨水就浸漫开来的那种稿纸;那种稿纸会使我写诗中断,情绪纷乱。”作者初学写作时有个毛病:一有觉得要改的字句,就一定要换一页纸从头写起,团成的废稿纸扔得满地都是。有一次外婆来作者家看见觉得可惜,就说:“你想好了再写。”五十多年过去了,外婆的话还仿佛在耳边。信件或文稿如果要留底,要么抄录,要么用复写纸——可以垫两至三张,现在还留存着作者父亲有些文稿是复写的手迹。作者父亲爱用钢笔、蓝黑墨水;墨水还有纯蓝的,绿色的表示亲密,红色的表示绝交。作者二哥那时跟国手过旭初、过惕生兄弟学下围棋,打棋谱用的圆珠笔,用红蓝两色代表对弈双方。
作者拉杂聊了许多,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就像《北京商品目录》“说明”中所说:“本目录列入的商品在供应上基本分为统购统销、计划供应分配、市场自由选购三种主要方式。”并不是所有著录的商品一般商店都能买到,厚厚的一册中有许多内容作者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总的来说,过去的普通日常生活与如今相比,无疑更加拮据、匮乏、艰辛;但回味起来,却似乎有一种更实在、更完整,在我们度过的每一天里占据一个更加无法忽视的位置的感觉。作者年轻时曾自学中国哲学史,明代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很合作者心意。如今再翻看《王心斋先生遗集》,《语录》中有云:“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作者个人的心得是,“百姓日用”应当涵盖统而言之与具体而微两个层次,并不局限于作者上面所说的内容,但也不排斥这些。
本文通过《北京市商品目录》及相关回忆,展现了老北京百姓过去的日常生活,包括各种生活用品的使用、手艺人的活动等。尽管过去的生活有诸多不便,但其中蕴含着一种实在和完整的感觉。作者借明代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表达了对过去平凡生活的珍视和感悟。
原创文章,作者:Weaver,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anghehb.com/19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