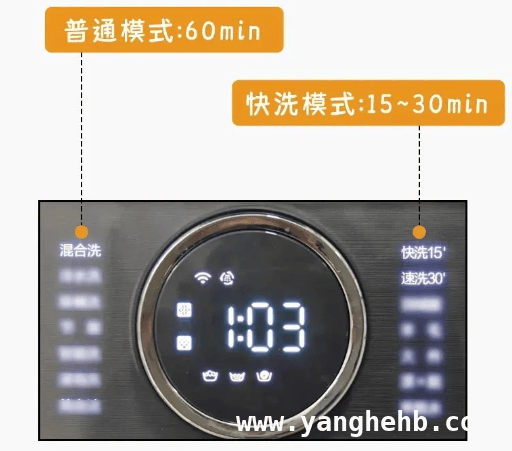本文围绕李慈铭的日记展开,讲述了民国年间其日记稿本辗转沪上后遭遮蔽、涂抹的情况,介绍了陈乃乾对日记的校补工作,以及李慈铭本人的一些日记内容和他与陈豪的交往信件,探讨了日记被删文字的原因,还提及早期传抄本对复原日记原貌的重要作用。
在民国的文化江湖中,有一位以“毒舌”闻名的人物,他便是李慈铭。民国时期,他的日记稿本几经流转来到沪上。当时,经营《越缦堂日记》石印出版的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还有藏家、读者,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对日记进行了遮蔽、涂抹。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日记的完整性,还让李慈铭无端蒙上了隐没墨迹、惺惺作态的负面形象。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馆员张桂丽,在“谁动了李慈铭的日记”这组文章里,打算结合李氏日记稿本、抄本以及书信、诗文稿,通过时空坐标、人际网络以及李慈铭心态的变迁,来还原日记稿本中一些被删文字所处的历史场景。
民国三十二年(1943),《中华月报》第6卷第1期刊载了陈乃乾的《之□》一文。陈乃乾在文中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民国九年蔡孑民先生从李氏后人那里商借,用原稿石印,随后便在海内广泛流传。只是其中有诋毁他人之处,常常涂抹掉人名。蔡孑民先生宅心忠厚,自然是想隐恶扬善。但读者因此百般推测,反而产生了更多误会。去年李氏原稿出售,我借来放在案头半个月,拿石印本进行勘对,凡是被涂抹的字,都进行了校补,现在摘录出来,供读者了解。李慈铭恃才傲物,他表达爱憎的言语,不能当作定论。要是能在日记中附上人名,那肯定比名字被埋没无闻要好得多。倘若他泉下有知,应该不会认为我多事。”
陈乃乾的这番话,代表了当时不少读者的心声。确实,李氏日记石印之后,因为多处被涂抹而遭到讽刺,“转滋误会”。鲁迅先生在1927年就曾抱怨道:“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鲁迅全集》第四卷《三闲集·怎么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然而,这些遮掩、涂抹的行为,究竟是李慈铭本人瞻前顾后、欲说还羞,还是后人进行的再加工呢?
李氏日记对陈乃乾来说,有着不可言喻的魔力。他曾耗费大量心血,将《越缦堂日记》中零散的读书札记进行整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辑成十二卷。他在1931年7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把我所辑的《越缦堂读书记》稿共九百卅七种卖给富晋,得到三百元。”(《陈乃乾日记》,陈乃乾著、虞坤林整理,中华书局,2018年,第45页)当时他阅读的是民国九年(1920)石印的《越缦堂日记》,案头摊开的这本日记,纸页间墨迹斑驳、涂改的痕迹纷杂,读起来每每让人触目惊心。机缘巧合之下,他从友人处借得一部待售的李氏日记稿本,两相对照时,忍不住做了一番索隐工作。最终,他补出石印本人名阙字二十余处,包括张广川、章嗣衡、罗嘉福、傅子蓴、周星誉、钟佩贤、胡梅卿、孙祖英、钮玉庚、王受豫、陈凤冈、全懋龄、王嘉谟、任棻、鲁元杰、吴宗峻、李雅斋、李国琇、李谦、何炳荣、李萼棠、李孝政、李孝莹,这些人大多是李氏的乡人或族人。

上文提到的李慈铭日记部分,有四行被墨涂。
这年三月,李慈铭参加会试,四月十一日放榜,日记记载:“当天公布红录,云门、紫泉都考中了,绍府一共中了五人,山阴有三人,分别是程仪洛、潘遹、俞麟振。庚午同榜只中了一个杭州人蒋某,我实在不忍直视。国家选拔人才到了这种地步,让我还和这些人竞争,还能说我有脸面吗?”(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民国石印本)而他的门人樊增祥高中进士,无疑加剧了他“腼然人面”的屈辱感。两天后,李慈铭从礼部拿到自己的考卷,发现被编修臧济臣点抹,他非常愤怒,痛骂道“鼠辈何足责哉”,心情糟糕透顶。
其实在前一年,李慈铭的戾气就很重。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写了回复陈蓝洲的信,大约有数千字,都是论述近日官吏的危害以及励品守道的要点。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是激愤,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是孤介,然而这实际上是中庸不变的道理。我自己规定了杜门七例:一是不回复外官,二是不结交翰林,三是不礼遇名士,四是不与富人交往,五是不认天下同年,六是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是不参与婚寿庆贺。这些都是为了矫正世俗的偏差,挽救末流的过失。我所说的翰林名士,也只是指今日的馆阁庸才、江湖小人,按照我的性情对待他们,实际上并非过于偏激。恐怕蓝洲读了这封信,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民国石印本)这里的“杜门七例”堪称极端的社交洁癖,也是李慈铭名士气质的绝佳注解。当时京官们都疲于应付这些社交琐事。
陈豪次年六月末的来信中,有不少规劝李慈铭和光同尘的话。当时正值放榜后几个月,很容易触动李慈铭敏感的神经。而且陈豪作为外官致赠六金,既违反了李慈铭“不答外官”的规定,他的规劝又触犯了“不交名士”的忌讳,这种双重越界必然引发李慈铭的反感。
他是否把陈豪的原信和六金退还,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到了后一年,光绪四年,他再次收到陈豪的信,九月初四的日记记载:“收到云门的信和陈蓝洲的信,蓝洲卸任房县代理县令后,也接到檄文去宜昌监厘局任职了。”此时他已不再恶语相向。光绪六年十月,陈豪又寄来十二两银子祝贺李慈铭考中进士,次月李慈铭回信说:
蓝洲仁兄同年足下: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并非我故意疏远。志同道合、坚守操守的人,天下能有几个呢?况且我们在乡国交往,贫贱时相互体恤。如今远隔燕楚,浮沉于中外,我已年老,您也不再年少,难道会因为言语上的小节就导致关系破裂吗?实在是因为近年来我病得厉害,很少写信,又觉得自己没什么可以回报故人的,您不会埋怨我吧?
前年承蒙您赠送廉泉一流,这种赠礼不在于多,更何况您损自身清风,来关怀远方之人,对我的关爱已经很多了。今年朱子云来,又承蒙您寄来分俸,伯夷之粟,出自您手;言辞恳切,对我念念不忘。敬谢,敬谢。
想来您在应城为官,如同琴鹤相伴,和山居生活没什么不同,岁末事务清闲,治理政务也有很多闲暇。我三十年科举之路,才获得一第,没想到在晚年,还能追逐桃李般的春光。我历经挫折,老态龙钟,实在不能涂脂抹粉,跟着馆阁后生们登场作态。因此我极力请求仍归原官,这并非矫情,也不是玩世不恭。至于那些追逐名利的行为,实在是万不得已,我怎么会在此图捷径、争先机呢?外面的人议论我、嘲笑我,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是愤激,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是恬淡退让,您看呢?
仲彝在家守孝,辛梅在吴中任县令,云门改任官职,竹篔出使长安,昔日的琴尊之侣,如今已无一人。松溪在庐陵,仲修在全椒,听说都因落寞而罢任,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我很挂念。倘若有机会传递书信,还望您不要吝惜消息。特此敬问您的起居。不多说了。弟慈铭顿首。十一月廿八日。

李慈铭致陈豪信札首页影印
李慈铭不仅在信中对老友分俸之事表示感谢,更坦诚地剖白了自己的内心。他自辩虽然言辞犀利,但并非绝情之人,并坦言自己甘愿做户部俗吏,是因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难以胜任清要之职,所以拒绝进入翰林院。信的末尾,他还和陈豪分享了陶在铭、羊复礼、樊增祥、许景澄等朋友的近况,字里行间尽显真挚的情谊。
这封信被陈豪精心收藏,他的儿子陈叔通将其辑入《冬暄草堂师友笺存》。该书共收录了李慈铭同治七年至光绪八年间的信札三十九余通,这些信大多是交心之言,友情真挚,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氏的日记本中多是率性之词,这则被删的日记,不过是他一时的激情之言,并无大碍,不知是谁擅自抹去。陈乃乾当时所能见到的李氏稿本日记,是民国九年(1920)石印《越缦堂日记》的底本。尽管这部分稿本现在藏于上海图书馆,但上面不仅有蔡元培签批“某处去某字”,还有多处墨涂。陈乃乾披露的被删文字,不禁让我们深思:这些被涂抹的文字,究竟是李氏自己为了粉饰而做,还是后人打着“为贤者讳”的名义擅自修改的呢?
所幸的是,李氏日记有孙咏裳、平步青、杨樾、王彦威等九种早期传抄本。这些避忌时政的抄本完整地保存了李氏对人物的尖锐评价,在现存稿本遭到系统性删改的情况下,它们恰好成为复原日记原貌的关键证据。
陈乃乾保存下来的这则李氏日记佚文,既为重建李氏日记文本原貌提供了证据,也揭示了稿本文献——尤其是近代日记——在流传过程中的文本破坏现象。近世学人常常以道德裁判者自居,对日记中不当、不雅的言辞任意删减,这种违背文献存真原则的篡改行为,不仅混淆了史料的真实面貌,还让作者本人遭受了不白之冤。
本文围绕李慈铭的日记展开,讲述了其日记在流传过程中被遮蔽、涂抹的情况,通过陈乃乾的校补工作和对相关日记、信件内容的分析,探讨了被删文字的原因,强调了早期传抄本对复原日记原貌的重要性,同时批判了近世学人违背文献存真原则的篡改行为。
原创文章,作者:Robert,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anghehb.com/9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