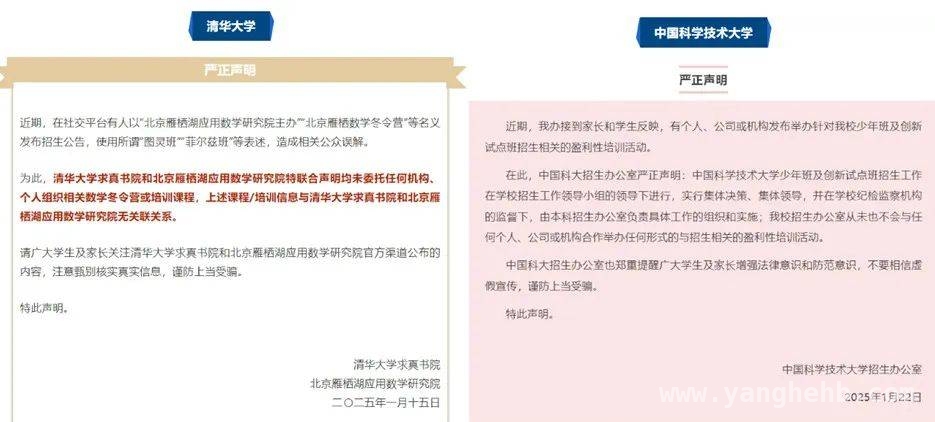本文围绕投资界与DeepSeek的故事展开,多位知名投资人分享了寻找DeepSeek的经历,探讨了其对科技投资带来的反思,包括资本市场回暖、创新资本定价、投资模式挑战等问题,还展望了未来的创新投资机会。
五源资本创始合伙人刘芹回忆起一年多以前的经历,感慨道:“我当时找了三拨人,一心想和梁文峰(DeepSeek创始人)见上一面,可他却拒绝了。”一旁的元禾璞华管理合伙人陈大同打趣地说:“我的待遇比你稍微好一点,我们和DeepSeek的人有过交流。他们觉得我们的投资领域和芯片相关,所以给我们开了一条小缝。”
如今,DeepSeek火爆出圈,成为科技界的焦点。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整个投资界竟没有一家能成为它的股东,很多投资人甚至连和DeepSeek交流的机会都没有。在3月22日举办的亚洲青年科学家基金项目探索科技新前沿论坛上,多位投资人纷纷谈及DeepSeek,并分享了这次经历给科技投资带来的深刻反思。
元禾璞华管理合伙人陈大同指出,对于当前的风险投资而言,没有商业模式的DeepSeek很难成为合适的投资标的。北极光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邓锋则强调,要将社会资本和政府资本结合起来,探索一种更具创新性、更能容错的投资模式,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创新项目。否则,可能会再次错失像DeepSeek这样的潜力项目。
以下为圆桌实录,略有调整。

多位投资人围绕DeepSeek展开讨论,并分享了对科技投资的反思。
DeepSeek的出现,重新建立了资本市场对中国科技创新的信心。
刘芹(未来论坛理事、亚洲青年科学家基金项目捐赠人、五源资本创始合伙人)提出问题:“春节后资本市场开始回暖,很多国际投资人都在重新评估中国科技公司的价值。在各位看来,这次中国资本市场的回暖是否可持续呢?”
邓锋(未来论坛理事、北极光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认为:“从长期来看,是可持续的。资本市场回暖受多种因素影响,DeepSeek是一次颠覆式创新,这里的颠覆并非单纯指技术,实际上它是工程上的优化。DeepSeek的成功表明,中国企业能够通过工程优化把模型做好,这极大地提升了大家对中国科技公司的信心。从长远角度看,中国在科学研究、工程创新和产业转化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
刘芹接着说道:“你的意思是,资本市场的长期可持续性源于中国在科学研究、工程创新和产业转化方面的优势得到了认可。”
陈大同(未来论坛理事、亚洲青年科学家基金项目捐赠人、璞华资本/元禾璞华管理合伙人、投委会主席)分析道:“DeepSeek看似是偶然事件,实则迟早会发生。它通过工程上的创新,使算力效率提高了数倍。事实上,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创业公司中并不缺乏这类创新,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二三十年了,我们做投资就是要挖掘这类创新项目。”他还指出,中国有两大优势,一是产业优势,二是人才优势,尤其是算法方面是中国人的强项。对于资本市场回暖,他长期看好,但认为短期内一两年内可能会出现起伏。他还表示,多年来资本定价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西方手中,这次DeepSeek的成功是一个突破口,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观念上的变化。
刘芹表示:“中国创新资本定价的叙事正在改变,话语权或许正在转移,这个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但长期性是由基本面决定的。”他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大模型引发了大学教授的普遍焦虑,因为人工智能的这次创新范式与以往的科学研究范式有所不同。以往科学研究大多在大学进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进入产业界,但AI的这次创新很特殊,研究实验需要大量算力和资金,同时还需要很强的工程能力,科学研究、工程产业化创新迅速浓缩在一个环节。这对我们的投资判断和投资评估项目的模式会带来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应对呢?”
邓锋回应道:“以前大家常说科技成果转化,我认为这个词不太准确,我一直强调产学研结合。如今科学和工程高度浓缩且迅速迭代,如果按照以往的模式,实验室做出成果后再尝试量产,风投再介入,迭代速度就会跟不上,无法形成闭环。从投资角度看,我们肯定要往早期投资,但颠覆式创新是难以预测的。投资讲究概率,而真正的颠覆式创新无法预测,比如可控核聚变是大方向,但有很多不同的技术路线,哪个能成功还不确定。所以投资不能只押注一个领域。而且有些项目需要15年才能成功,让风险投资现在就投入是不现实的。”他还从社会层面指出,这些项目的投资是个难题,政府直接投资失败率太高,VC又担心延长周期。他提出思考,中国能否借鉴类似OpenAI的模式,但不一定完全相同,开展商业化相关研究,可能需要和大学合作,这需要大家共同探讨。
陈大同也认为:“风险投资现有的资本结构无法支持颠覆式创新。我们看到的颠覆式创新往往是一项技术在全世界都没有,而中国做出来了,但这种创新基本不会出现在企业,因为企业要考虑在三到五年内变现,不会去做10年、20年才能变现的创新项目。”他还提到,很多颠覆式创新都出现在大学里,一二十年时间可能会孕育出一些全世界都没有的好东西。但目前面临0 – 1的问题,只有技术,没有团队和公司,如果让他们自己去孵化公司,很多好东西可能就会被浪费。所以要真正颠覆市场,需要一种全新的资本结构。
梁颕宇(未来论坛理事、亚洲青年科学家基金项目捐赠人、前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分享道:“大概五六年前,我就在思考中国的创新从何而来。美国很多创新来自学校,而中国过去一直以产业创新为主,但后来我发现创新也在学校里。于是五六年前我带着团队去各个大学孵化公司,包括北大、清华、交大、复旦、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目前成功率大概在70%左右。”她还指出,帮助企业家、科学家转化成果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他们发现教授们让听话的学生做CEO基本都会失败,如果找能帮助商业化的人做CEO,成功率会大大提高。
邓锋对青年科学家和海归科学家充满信心,他说:“现在的青年科学家和海归科学家头脑中有商业概念,他们在创新时会考虑应用场景和商业化实现方式,这和以前很不一样。我非常看好这一代科学家,如果学生到企业里锻炼后再回来,再结合投资人的力量,同时改变投资模式,我对中国的科技创新充满信心。”
刘芹感慨道:“人工智能的范式变化对我们的投资范式冲击很大。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错失了DeepSeek。我一年多以前找了三拨人想和梁文峰见面,他拒绝了,意思是我们是资本家,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有人争议,DeepSeek可能是很好的创新力量,但不一定是好的投资标的。抛开这个不谈,大家对整个行业错失DeepSeek,甚至连交流机会都没有,有什么反思呢?对于下一代创新投资机会,大家会关注哪些行业和细分领域呢?”
陈大同回答:“我的待遇比你好一点,我们和DeepSeek的人聊过,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投资领域和芯片相关,所以给了我们一点交流的机会。但即便如此,我觉得我们这种基金也很难真正投资进去,因为它的模式和我们相差太远了。”对于创新投资机会,他认为AI是不可错过的热点,行业AI或产业AI是他们最关注且擅长的领域,会大量投资,但不会投资从0 – 1的项目。他还指出,AI只是中国创新的一部分,中国的创新涉及多个领域,AI占比可能不超过10%。他预测,未来中国的创新会非常激烈,不创新就难以生存,这将改变全世界的创新模式。
邓锋表示:“我们虽然错失了DeepSeek,但并不后悔或难受。在投资中经常会错失很多项目,关键是要看是不是我们该赚的钱。按照我们基金的运作方式和投资逻辑,DeepSeek项目即使来了,可能也无法通过,因为它还没有商业模式,无法进行投资。投资中最后悔的是投进去了,却在不该退出的时候退出。”他还分析了DeepSeek给投资带来的几大影响,一是应用迅速靠近,大家会聚焦在应用上;二是数据创新是个好机会;三是基础设施会有创新;四是AI和其他垂直领域的结合,如制药。他强调,要解决社会资本和政府资本结合的问题,探索更能容错的创新模式,否则可能会再次错失类似的潜力项目。
梁颕宇回忆道:“大概在2016年、2017年,我觉得中国的临床做得不错,但研发创新药需要更多工具。于是我们开始寻找相关工具,2017年投资了人工智能新药研发,通用人工智能也在同年开始投资。我认为未来AI和医疗还有很多结合的领域。”
本文通过多位投资人对DeepSeek的讨论,展现了投资界在科技投资方面的思考与反思。从资本市场回暖的可持续性,到创新资本定价话语权的转移,再到投资模式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创新投资机会的展望,都反映出科技投资领域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强调了要结合社会资本和政府资本,探索新的投资模式,以适应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抓住更多创新项目的投资机会。
原创文章,作者:Juliana,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anghehb.com/42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