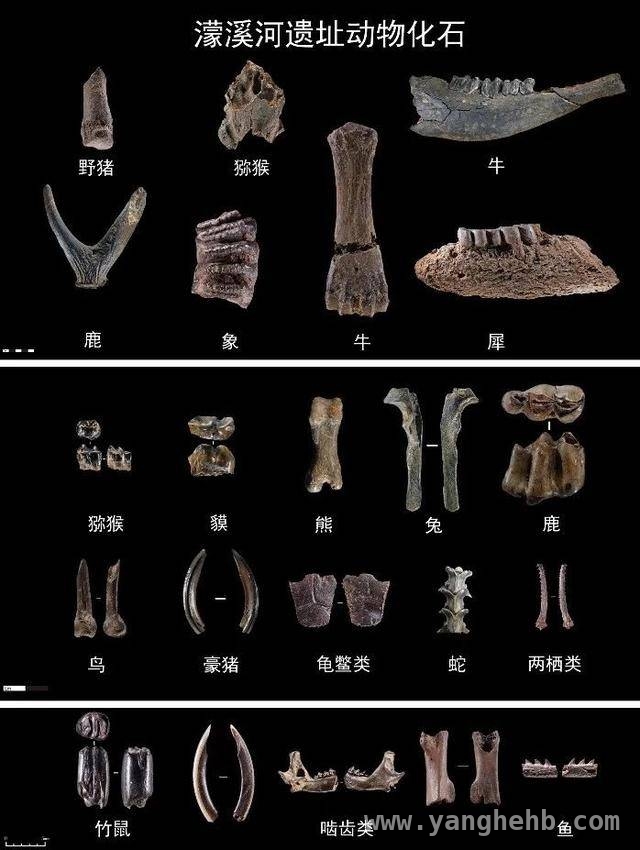“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展览展开,介绍了展览的基本信息、艺术家余友涵的生平与艺术成就,还通过对展览策划人赵剑英的专访,深入探讨了展览策划考量、余友涵艺术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系等内容,同时提及在深圳办展及深圳艺术周的相关话题。
近日,一场备受瞩目的艺术盛宴——“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展览在深圳美术馆盛大开展。此次展览由深圳美术馆主办,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协办,由策展人与艺术史学者刘鼎和卢迎华共同精心策划。
展览全方位呈现了上海艺术家余友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精彩创作生涯,现场展示了100多件作品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余友涵先生离世后的首个大型回顾展。展览通过余友涵早期实践与晚期创作之间的深度对话,巧妙地展现出其内在变化的思想肌理,使得艺术家的个人生涯与中国当代艺术自身发展及其背后的思想流变形成了独特的互文关系。而且,此次展览也是2025深圳艺术周重要的展览项目之一,展览将一直持续至7月10日,为广大艺术爱好者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去欣赏和品味。
南都记者亲临展览现场进行深入了解。余友涵于1943年出生在上海,此后一直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直至2023年离世。1973年,他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余友涵被公认为中国当代重要且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的绘画实践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堪称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先驱。余友涵巧妙地融汇了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刻理解和西方艺术的独特表达方式,通过对各种视觉手法的不断探索,他的绘画具有普遍意义,深深地影响并感染了一代年轻艺术家。
在展览现场,南都记者对此次展览的策划人、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赵剑英进行了专访,就如何在深圳推出重要艺术家展览以及如何更好地营造深圳艺术氛围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南都:这次展览选择艺术家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两个时段的重要作品展出,是出于什么考量?
赵剑英: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的“应:中国当代艺术史研究计划”,始终希望与那些具有“历史化的能力”与“理论化的勇气”,同时视角能深入历史具体肌理的研究者与机构携手合作,为历史提供艺术的坐标。刘鼎和卢迎华这两位策展人的研究工作,一直是我们长期关注且深受感召的。这个展览最初从我们委任的个案研究起步,最终发展成为如今的精彩展览。在个案研究过程中,艺术史学者和策展人刘鼎和卢迎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长时空”、全景式的视野,他们深入分析了余友涵的创作历程与内在展开逻辑,为不同阶段作品变化的基本轮廓和不同侧面提供了独到的解读。
他们将余友涵的早期经验和晚期风格之间的内在关系,巧妙地处理为“互为前史”的互文性重构——以余友涵在新潮美术时期所在的特殊位置,作为其一生思想变迁的枢纽。在代际互动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余友涵逐步将他“以西方现代艺术技艺来回应中国传统哲学命题”的重心,转向纯粹的绘画实验乃至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潜力的表达。由此,为他后期创作里“以圆作为容器”以容纳文化的多元命题的思想和实践,提供了语言和经验来源。这一进路,与“从文化怀旧到现代民族国家的重新想象”的历史格局变换之间亦存在着隐性的重叠关系。在此意义上,晚期风格不仅是一种萨义德所描述的晚期创作的特殊倾向,更是创作者抵抗时代之变与生命异化的诗学实践,正如刘鼎和卢迎华在文末所说,“余友涵的实践告诉我们:对自我创造进行探索可以一直进行到底。”
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本质上是“跨体系性”的
南都:你觉得艺术家余友涵的个人生涯与中国当代艺术自身发展及其背后的思想流变是如何形成互文关系的?
赵剑英: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本质上是“跨体系性”的,它既包含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又承载本土经验的地方性转化,更涉及个体在历史断裂中的创造性回应,是多重历史脉络、地缘关系与知识体系交织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余友涵先生是40后知识分子的一个优秀思想样本——从特殊历史时期之后的个人觉醒到参与新潮美术运动的激情澎湃,从对后印象派的深入研习到对波普艺术的巧妙转译,余友涵的创作不仅映射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复杂脉络,更揭示了艺术家如何在个体经验与集体历史之间寻找对话的可能;他在历史褶皱中开辟出属于自己道路的实践历程,既是对中国艺术史认知框架的挑战,也为当下提供了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代际之间互动关系与历史书写的珍贵样本。在展览中,策展人刘鼎和卢迎华发现了很多细微的思想线索,比如从一张静物画中出现的书籍《熵》,来探索他和“文化热”的联系;策展人还提出余友涵创作中未曾明确言说的与超现实主义的关联。这些个人的、隐秘的思想变化,背后都有中国当代艺术变革之下的思想流变作为前提。

南都:如果给观众推荐三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你会选择哪三件?其中的因由是什么?
赵剑英:我首先愿意推荐“圆”系列作品,这个系列的画面通过密实的笔触和色彩对比,营造出漩涡般的流动感,既呼应东方哲学的“阴阳”辩证,又融合西方构成主义的理性结构,这个系列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几乎件件精彩;然后,我愿意推荐余友涵先生一生唯一的装置作品,《会唱歌的邓丽君小姐》,这件作品是他在80年代参加“凹凸展”的参展作品,展览中我们展出的当时展览的现场照片是同事一个像素、一个像素把一张模糊的照片修出来的;此外,我还想推荐一件名为《对峙》的作品,虽然这件并非余友涵典型的代表作,但画面是余友涵之子余宇和父亲合作完成,造型的对峙中隐含着幽默的现实对应与情感,非常有趣和有爱的作品。
深圳从无到有的造城历史是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很重要的文化基础
南都:是什么原因促使你2022年选择在深圳开设第二家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的?
赵剑英:从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来讲,我们这一代的机构都很受益于黄专等当初来深圳工作的学者老师们,因为他们当时的一些工作,还有他们所开启的一些视野,某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方式和形状。同时,深圳从无到有的造城历史,恰好和中国当代艺术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从无到有的历史遥相呼应,同脉同频,这其实也是一种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很重要的文化基础。这两个进程的动力,关乎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我们也决心把我们的经验、资源、最好的艺术带到深圳来。所以,虽然我们十二年前创立于北京,但我们其实对深圳从来不感觉陌生,而是非常亲切的,可以说,“来了就是深圳的机构”,我们很快在这里交到了非常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帮助和鼓励。同时,深圳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城市活力。我居住在这里,和朋友们交流中感觉到深圳对更加多元的艺术场景需求很高。

南都:这次展览也是2025深圳艺术周的重要展览活动之一,你如何看深圳艺术周在当下深圳所起的作用?
赵剑英:较北京、上海的艺术区的聚集度而言,深圳的文化机构地图总是点状的、分散的,不过这也提供了通过遍访各个机构来探索整个城市的可能性,可以说,深圳艺术周比任何城市的艺术周都更能借由艺术周而走遍整个城市。每个机构的机会也在于此——在深圳还可以通过用功,让自身成为城市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我认为深圳艺术周,是最有潜力联动起一座城市的艺文内容的一个活动,这对于我们参与深圳艺术周的一员而言,必须百分之百努力、贡献最佳的展览,奉献给市民观众和远道而来的客人。
本文围绕“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展览展开,介绍了展览情况、艺术家余友涵的生平与成就,通过对策划人赵剑英的专访,深入探讨了展览策划考量、余友涵艺术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系,还提及在深圳办展及深圳艺术周的意义,展现了余友涵艺术的魅力和深圳艺术发展的潜力。
原创文章,作者:Ambitious,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anghehb.com/68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