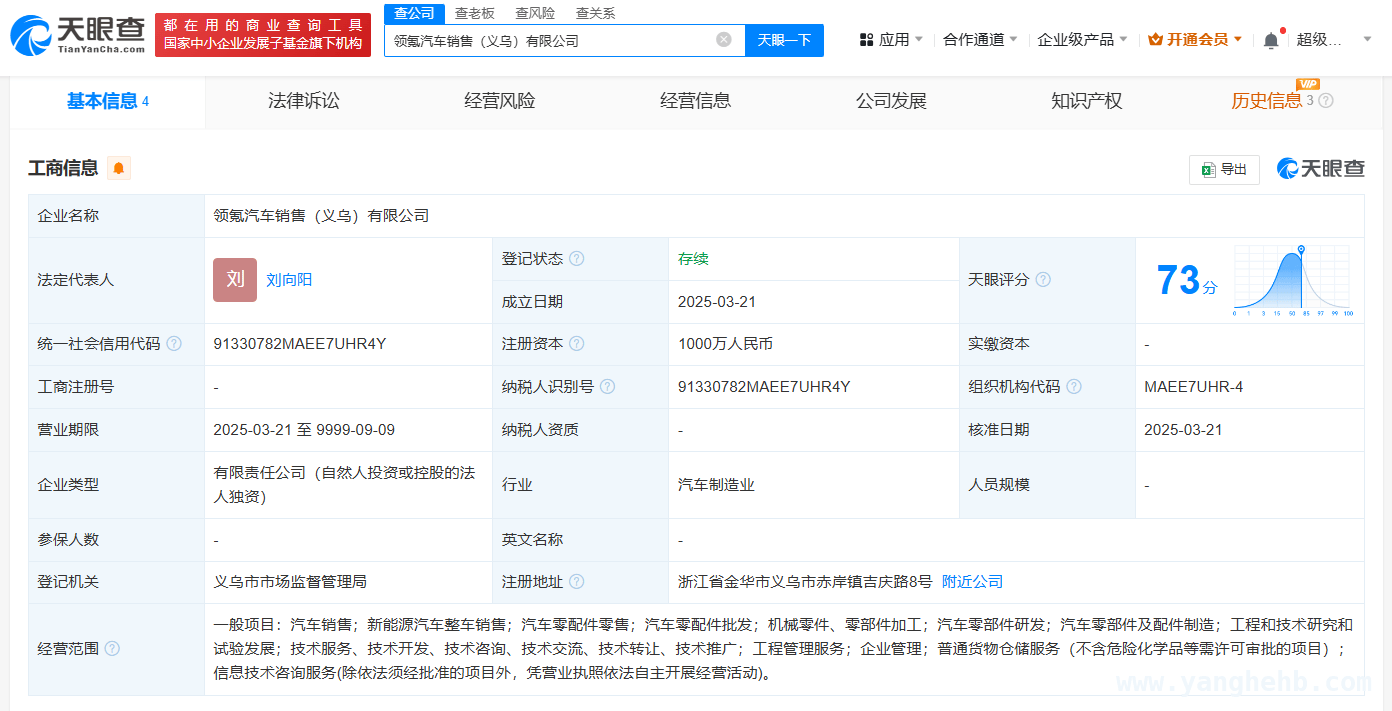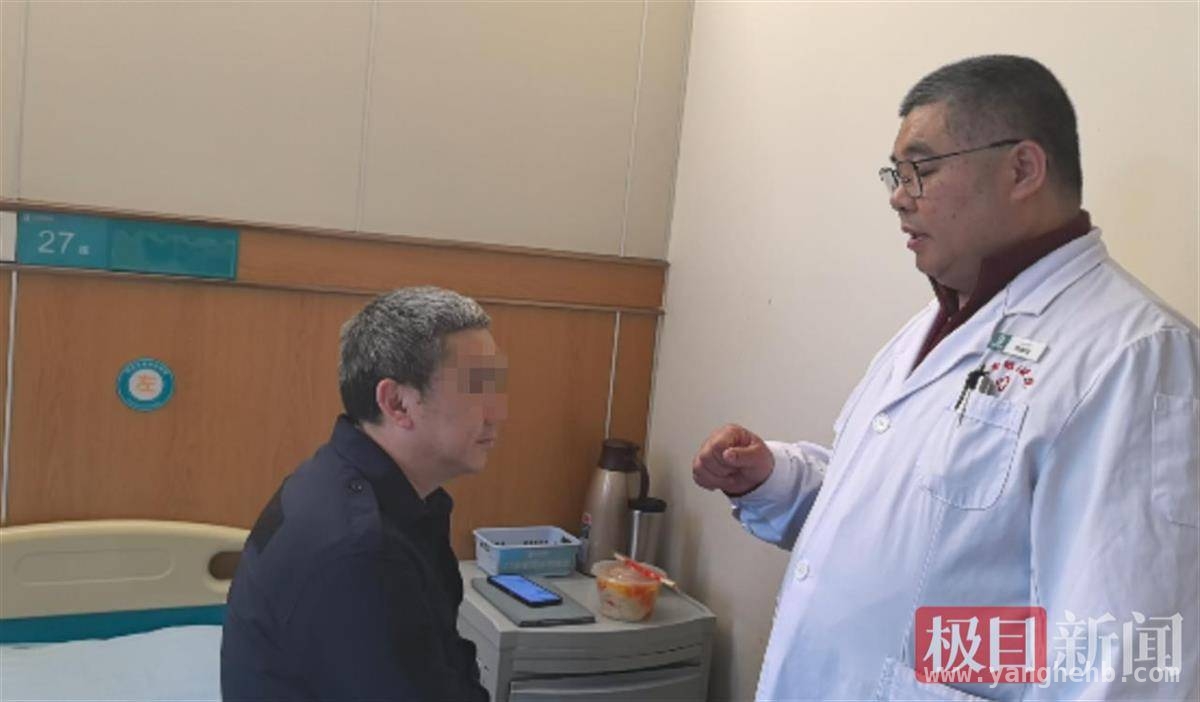本文围绕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新常态”展开,探讨了经济学创新需要平衡的三种关系,包括思想性与学术性、聚焦重大问题与追求技术严谨、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同时,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的新元素及其引发的重大问题,强调中国经济学者应抓住机遇进行创新,推动经济学发展。
学术研究新常态与经济学创新
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积极学习和借鉴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方法、工具以及学术规范,如今已然步入一种“新常态”。在这一崭新的常态之下,经济学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此,我着重指出,中国的经济学创新尤其需要审慎平衡以下三种关系: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系、聚焦重大问题与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既像是一种“得失交换”,又仿佛是一对对“矛盾”,稍不留意就容易顾此失彼。然而,奇妙的是,经济学创新往往就诞生于对这些关系的精妙平衡之中。
首先是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系。思想,代表着对问题的深刻洞察;而学术,则侧重于研究的规范性。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初期,中国的经济研究主要聚焦于学习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以及探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根本思路。那个时期的经济研究极富思想性,但学术性相对薄弱。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学术规范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思想性却似乎有所欠缺。缺乏学术性和学术规范,研究就难以具备科学性,学问也会缺乏坚实的根基。但倘若思想性不足,即便研究完全符合学术规范,其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我们所期待的经济研究,是“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完美结合,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其次是聚焦重大问题与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经济学者,他们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提出并深入研究那些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大局的根本性重大问题。尽管当时他们所掌握的研究工具并不十分精致,研究方法也不够严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重要的智慧。新一代经济学者在经济学技术功底方面有了很大提升,然而目前存在一种倾向,即多从文献和工具出发去寻找问题,而非从问题,尤其是重大问题出发,去寻找合适的工具以解决问题。基于文献和工具的研究方法本身并无过错,科学研究确实需要运用已有的文献和工具,特别是前沿工具。但如果仅仅从技术工具和手头的数据出发,去研究一些并无太大意义的小问题,那就偏离了研究的初衷。我们期望的是,在研究重大问题的过程中,能够运用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并得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最后是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中国相关的经济问题,对我们而言具有双重重要意义。一方面,它直接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领域;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熟悉中国经济运行的细节,掌握丰富的案例和数据,在这方面我们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然而,研究中国相关问题时,容易出现过度强调中国特色的情况,从而导致研究结果缺乏一般性,这无疑会削弱研究结果的影响力。如果能够将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中所发现的道理上升到一般规律,不仅能够为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做出贡献,还能反过来增强对中国相关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积极关注并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诺贝尔经济学奖往往更多地授予那些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在研究一般性经济问题上取得突破的学者,包括在研究工具和方法论方面的创新。这种一般性的突破,对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同样具有极大的帮助。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学创新
认真思考并妥善平衡上述三种关系,是实现经济学创新的一个关键方面。当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步入“新常态”时,中国和世界经济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成为推动经济学创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进入的“新常态”,是一个从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并进一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长期发展状态。与这一新常态相伴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目标的多元化,以及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实际上,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并非新鲜事,德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早已实现了这一跨越。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了两个有别于以往案例的新元素,即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这两个新元素将引发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并有可能产生具有思想性和一般性的研究成果。
其一,中国的规模导致了中国作为崛起的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国进入人均中等收入阶段与以往其他国家(如韩国)有所不同,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由于发达经济体以及受其影响的全球经济可能出现“长期停滞”的状况,中国相对较高的增速使得中国经济增量部分在全球经济增量部分中占据1/3左右甚至更高的比例,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中国的规模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商品市场和贸易的影响、中国改革和市场变化对全球货币、资本和人才市场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的崛起导致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这些都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问题。此外,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还有可能改变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大背景下,中国14亿人口的巨大规模以及中等收入水平,既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也提供了强大的创新供给,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回顾历史,20世纪初美国经济超越英国经济时,全国人口仅有7000多万。
其二,中国的制度引发了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中国经济制度的最大特点,也就是最显著的“中国特色”,体现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与商的关系之中。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像中国这样,政府如此积极地推动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紧密融合,并具有强烈的激励去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推动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政府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助力之手”;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也导致了部分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如果经济“新常态”意味着这种政商关系的转变,那么未来政商关系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家,以及如何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些都是经济新常态下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政商关系对经济的影响只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方面则是经济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这也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制度演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为验证已有理论假说和发展新理论提供了绝佳机会。从实证的角度出发,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有望推动经济学的创新。因此,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很可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对于上述两类由中国的规模和制度引发的新常态下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者具备一定的优势。然而,要使研究同时具备思想性和学术性,既能够抓住重大问题又符合技术严谨性,并且达到一般性的要求,就必须进行创新。
当前,世界经济学家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经济研究也应更加开放。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和方式,邀请世界经济学家与中国经济学家携手合作,共同研究由新常态引发的新问题,共同推动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我们期待中国经济学家能够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实现既有思想性又有一般性的经济学创新。
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新常态”下的创新路径。先是阐述了经济学创新需平衡思想性与学术性、聚焦重大问题与追求技术严谨、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这三种关系。接着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因中国规模和制度带来的新元素所引发的重大经济问题。强调中国经济学者应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创新实现研究的思想性、学术性和一般性的统一。同时呼吁以开放姿态促进国际合作,推动经济学创新,期待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历史机遇中有所作为。
原创文章,作者:Grayson,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anghehb.com/5833.html